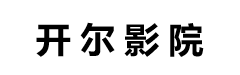2024年12月23日刊| 总第3824期
冬至,是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2024,是中国电影最冷暖跌宕的一年。
五位学院派影评人和五位民间影评人,赶在今年最长的黑夜到来前的几个小时,围绕着中国电影目前所面临的四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上演了一场激辩。

后排左起:梅雪风、李星文、胡建礼、宋方金、连城易脆;前排左起:吴冠平、索亚斌、陈亦水、闫怀康、翁旸
这场“2024中国影评人年末对话”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影视独舌》发起,不为辩对错、争输赢,只为综合学院和民间的多维视角,把当下中国电影最不容视而不见的问题拆解透彻。
活动由《影视独舌》创办人、影评人李星文和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索亚斌主持。学院派影评人有学院派的“武器”,民间影评人有民间的“高招”。众多观点的交锋、思维的碰撞,让现场火花四溅。

由于涉及具体议题时,学院派和民间派内部也很难达成一致,所以此次辩论并未采用组队方式。而是每个辩题由两派各出一位主咖,做10分钟的个人阐述。随后进入自由辩论环节,所有影评人、主持人,以及到场的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都可以参与到该议题的讨论中。
锣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发言吧。
如何应对短视频对电影的侵袭?
第一个辩题的主咖,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亦水,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

针对短视频对电影的侵袭危机,陈亦水开篇便指出,电影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充满了悲情色彩。随后她回溯了历史上电影所面临过的数次危机。
在电影全面取代马戏团,成为大众文化后,电视机、主机游戏、流媒体的出现,都曾给电影带来巨大的威胁。可是它们都没能取代电影,而是鞭策电影通过技术革新,走进了新的时代。
她认为短视频对中国电影的侵袭之所以看上去很可怕,让人担忧,是因为短视频契合了中国的时代症候——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思觉失调。与之相对,中国电影所显示出的脆弱,也更多的是因为其产业并不健全。
一方面,很多现象级作品依靠的仍是创作者个人的奋勇直前、赌上一切;
另一方面,某些电影宣发上带有投机心态的“神操作”,在杀鸡取卵。
因此,陈亦水认为短视频的侵袭,可能为中国电影带来一场休克疗法。往日荣光的虚假性得以暴露,产业就会来到转向节点。
胡建礼也开篇明义,指出短视频对电影的侵袭,实质上是对电影观众的抢占。

互动性和娱乐性上,电影不如手游;沉浸感上,电影不如VR;方便性和价格上,电影不如剧集。即便是电影一向引以为傲的视听效果,也被《黑神话:悟空》这样的3A级别的主机游戏比了下去。因此,短视频等新影像娱乐形态对电影观众的分流,是不可逆转的。
胡建礼进一步谈到了面对分流,电影的变与不变。他认为电影之所以为电影,是其有着自身的艺术审美标准和创作规律。 电影人绝不能在短视频等新影像娱乐形态的冲击下失去方寸,舍本求末。
短视频提供娱乐消遣和资讯信息,电影提供复杂的故事、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主题。事实也证明了,具有文学性,尤其能够通过精彩的对白、生动的人物和富有内涵的情节,触动观众的心灵,引发思考的电影,在短视频时代依然可以收获让人欣喜的票房成绩。
自由讨论时,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翁旸以老师的职业身份出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她指出短视频的出现,虽然给电影产业带来冲击,但它也“养活”了大量电影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以往只有少数进入头部电影公司的毕业生才能得到较好的实践机会,开启职业生涯。如今很多毕业生可以应聘或自组短视频工作室,学校无缝衔接工作。广义的短视频确实解决了很多年轻电影人的生存问题。

索亚斌反思了电影面对此次危机,技术革新上的几大突围路径。他认为如今仍处在瓶颈中的裸眼3D技术,最符合电影审美逻辑的发展方向。前几年好莱坞曾探索过的高分辨率、高帧率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震撼,但超出人的日常感知经验,很难成为视听媒介的常态。
此外,他还认为多线索、多结局,在影院里通过大家手机投票决定剧情走向的互动性,与电影作为被动接受艺术的属性相违背。互动性和仪式感,很难兼得。
舆情是在帮电影还是在毁电影?
面对四个议题中最具争议的一个,学院派影评人和民间影评人都派出了各自的青壮派代表——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讲师闫怀康和微博大V、市场专家连城易脆。两位立场鲜明、准备充分,用语言和思维大战了三百回合。
闫怀康抛出了“舆情”一词在定义层面的四大特征:直接、随意、隐蔽、偏差,由此指出其天然的负面属性。他的立场也就呼之欲出:舆情是在毁电影。

他首先指出网民不具备触发自律的环境,为舆情的泛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舆情会让观众对一部电影产生认知偏差,烙下思想钢印,还会引发群体极化的现象。这会让电影原本的优点被遮盖,极大地影响到票房产出。人们选择看不看一部影片,应该从对电影本身的了解出发,而不应该受到舆情左右。
其次,他指出了舆情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创作者会因为担心舆情而放弃创新,转向安全的主题和风格。创作者一旦进行自我审查,便会限制电影的艺术探索和表达自由。
最后,他借用损失厌恶理论,强调了舆情对电影宣发的破坏力之强。根据该理论,宣发要想扭转舆情的负面影响,需要付出2.5倍的投入。这可能就是大部分影片遭遇舆情后都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的原因吧。
连城易脆则认为舆情是舆情,电影是电影。舆情是电影之外的东西,因此当下电影对舆情的恐惧,很多时候是心理作用。因为他研究了很多案例后,发现有很多舆情并没有毁电影,甚至还会帮到电影的情况。

第一个例子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当年因为宣传不当而引发舆情,但是几年过去后,该片豆瓣评分回升到6.9。这说明后续观众,可以回归到对电影的理性评价。毕赣的新片《狂野时代》无论在业内外都备受期待,也说明人们并不会因为舆情而去否定导演。
第二个例子,《雄狮少年》的票房普遍被认为是受到了舆情的影响,才没有达到预期。可是统计过往几年12月上映的国产动画片,会发现《雄狮少年》是唯一一部票房过亿。12月中旬是学生的备考期,动画片的票房天花板本来就低,《雄狮少年》的不及预期更大的原因是预期定高了。

第三个例子,《好东西》爆发舆情时票房在4亿左右,猫眼专业版给出的总票房估算是6-7亿。如今该片票房已超6亿,总票房估算上调至7亿多。可见,舆情并没有对它的票房后续表现产生影响。
此外,连城易脆还提到有时候借助舆情,可以向大众普及偷票房、票房分账、盗摄等知识或观影礼仪,能有效避免同类舆情或不文明行为的再次发生。
自由讨论环节,编剧、作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方金率先发言,直指有些人看到舆情可以伤害电影后,怀着险恶用心主动引战。他认为围绕电影的营销、宣传、评价、讨论,都应该就着电影本质。舆情的危险之处在于将其引向了社会层面,且极不可控。

胡建礼指出,舆论与舆情是两个概念。舆论上升为舆情,就意味着在大众的理解中是负面的了。舆情的责任不在于舆情,而在于整个社会氛围。上世纪90年代末的电影也经常引发热议,就不会上升到现在的这种舆情级别。
资深媒体人、影评人梅雪风也表达了对不实营销、夸大式营销带来舆情反噬的担忧,并表示这消耗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信任。
电影人才匮乏的要害在哪里?
民间影评人坐镇这个议题的是擅长脱口秀的宋方金,学院派自然不敢怠慢,最终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吴冠平亲自上场。
宋方金一上来就火力全开,直言:“电影人才匮乏的要害在于不要害人才。”
他先是从宏观上阐释了电影人才的匮乏程度。他认为,仅依靠目前从业的电影人,中国电影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拨人能做到的已经都做了,既创造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

那么中国电影亟需什么样的人才呢?
宋方金第一个提到的是战略人才。他指出因为电影市场的盘子太小,所以像雷军这样能够去整顿一个行业的战略人才是看不上电影的。这使得中国电影现在依然处在农耕文明时代的熟人社会。
第二个是编剧人才。宋方金认为是电影行业对编剧的不够尊重,甚至还普遍存在一些伤害性行为,导致一流的编剧不愿意写电影剧本。他将编剧形容为“电影户口本上的户主”,本应对这部电影拥有解释权及著作权。海报上没有署名等行为,会逼迫优秀的编剧人才离开电影圈。
第三个是导演人才。他认为目前中国电影导演普遍缺乏类型片知识和综合素质,还批评了一些年轻导演通过翻拍外国电影“走捷径”。
最后宋方金呼吁电影要与其它文娱产品“生殖隔离”,要把电影本身的特性做出来,让电影更加电影。
面对犀利的宋方金,吴冠平尽显学院派的儒雅,有条不紊地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点,当下中国处于知识范型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掌握知识的人所能够施展的领域,还在重新认知,对认知人才有一定的模糊和变动。尤其是电影人才这样大的概念,就缺乏了细分的可能性。
第二点,过去编剧、导演、演员的职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行业,精英占比都是二八定律。人才是要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教训,最后成就的。也许今天在新兴领域中施展拳脚的人,十年后就成了电影圈创造奇迹的人才。
第三点,人才是会干专业活儿的,还是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个事情有时候会让我们晃神。其实,不同的场域里需要不同的人才。他们能在同一个行业的不同部分贡献自己的价值。
最终吴冠平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电影人才是否匮乏可以暂缓下结论。
2024年电影究竟在焦虑什么?
本次对话的辩题遵循了由微观到宏观、由封闭到开放的逻辑。面对最后一题,学院派影评人代表翁旸和民间影评人代表梅雪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破题思路。翁旸从三个维度的市场数据出发,探究市场视角的焦虑;梅雪风从不同导演群体今年作品的变化出发,探究创作视角的焦虑。
翁旸指出相比往年,2024年总放映场次在增加,而总观影人次在降低,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结构变化。企业端数据显示,影视公司多数在赔钱;项目端数据显示,成功备案的电影项目在减少。

这些市场数据引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未来两三年,影院里能看啥?
不过翁旸认为,人均年观影人次不足1所带来的焦虑,也可能成为激发潜能的触发器。她观察到,很多院线已经在设法自救。于是她介绍了美国、韩国等地影院的盲盒电影、纪念票根等玩法,希望影院能找到更多留住观众、召回观众的办法。
梅雪风从创作的角度对2024年上映的电影进行了复盘。 他觉得虽然2024年的市场数据比较惨淡,但这一年上映的电影,在艺术水准、文化价值上并不差。尤其是票房榜前列的几部作品,让他对中国电影并不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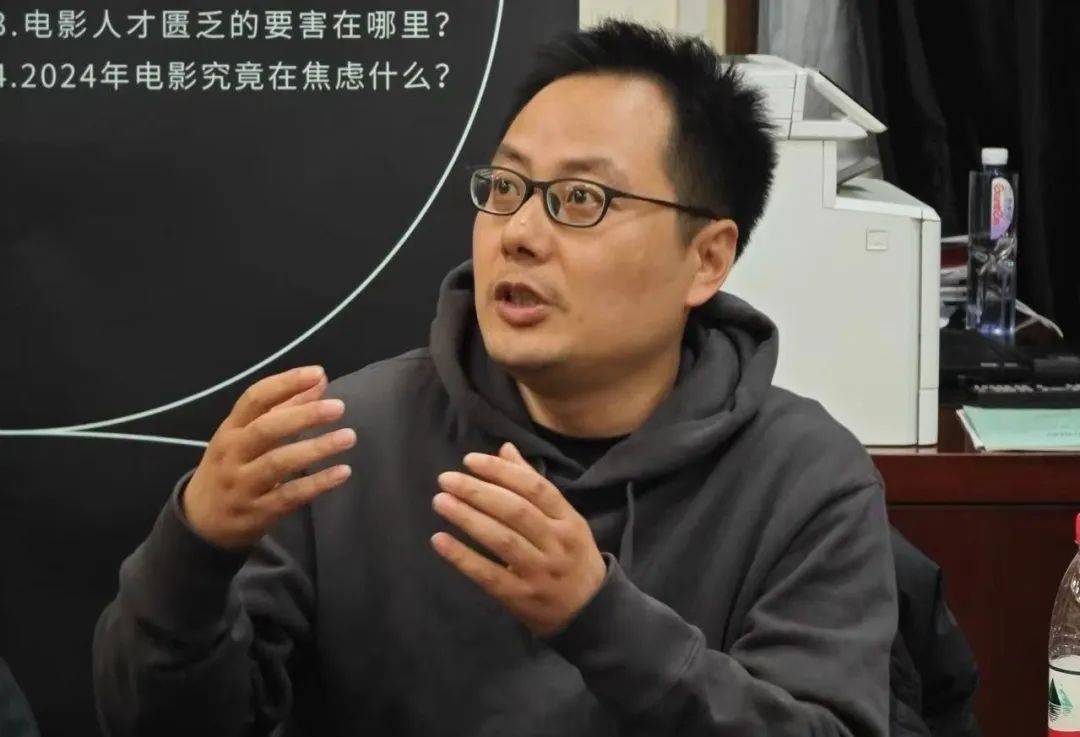
整体印象上,梅雪风指出今年第六代导演看起来像在一个退休的状态,第五代反而是年纪越大越像年轻人一样。女性创作者像真正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非常强的表达欲。几位年轻的男性创作者,反而在审美趣味上更像是中年人。香港电影新生代导演和中生代导演创作路线的分别显得越来越明显。
随后他分别对这几个导演群体的具体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描绘出他们的群体共性,让人们领略到一线电影导演们仍然在坚守与开拓。
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从年初跨年档、春节档、清明档连续三个档期打破影史票房纪录,到暑期档断崖式下滑,全年票房难以突破450亿,可谓大起大落。于是,一些“问题”愈发显得“很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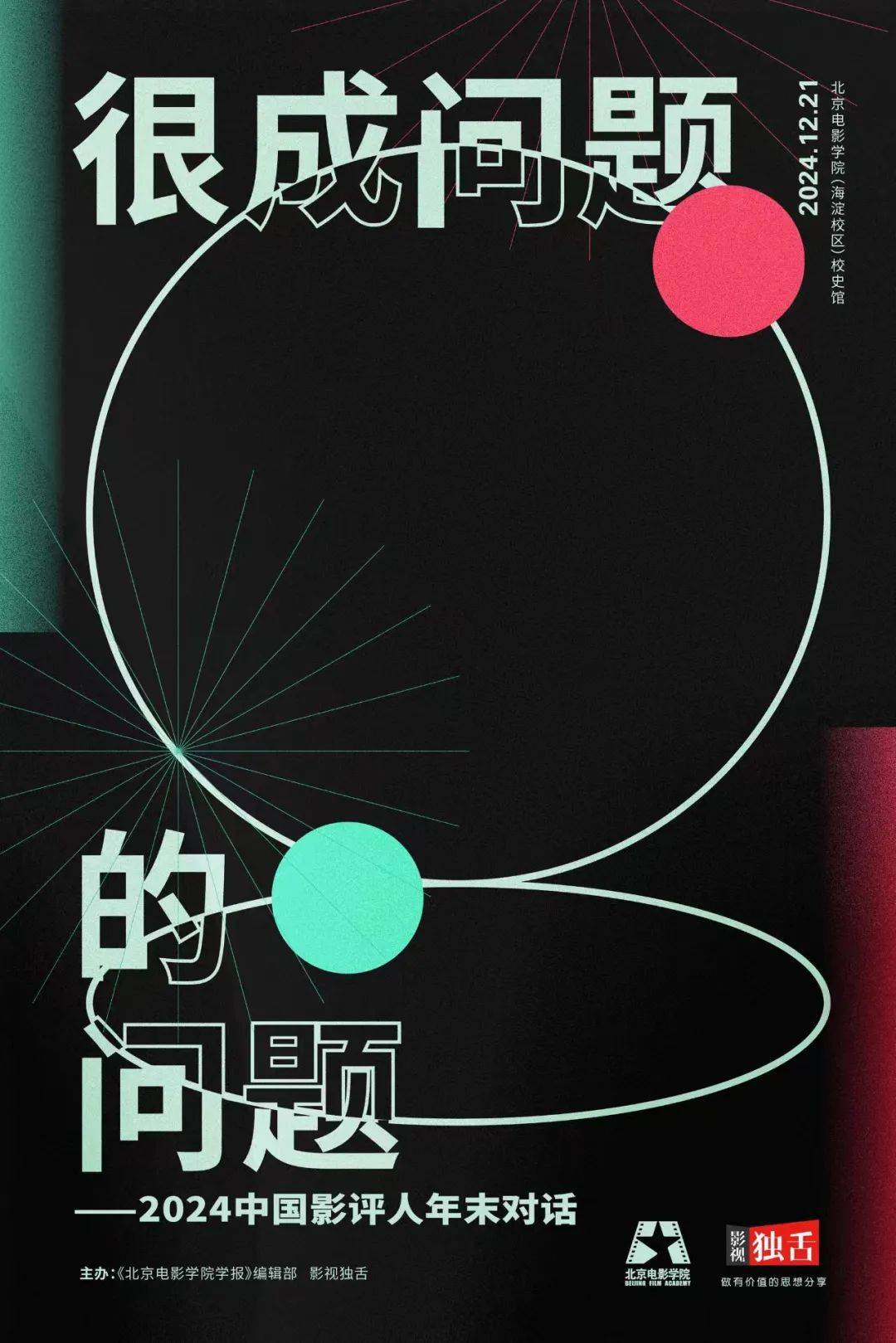
这场年末上演的影评人对话,让学院派的研究和民间的观察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从更多的视角去看“问题”,就有机会换位思考,将其探讨得更全、更深。黑夜的长短周期有律,电影市场的冷暖也一定是的。
【文/满囤儿】